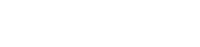“公孙瓒是如何筑起这么多高楼的?”荀攸指着地图上密密麻麻的圆圈说道。每一个圆圈就代表一座高楼,粗略一看,至少有大几百个。
“当年被他俘虏的青州黄巾。”阎柔说道:“三十万人,最后剩下的不到三成。那些黄巾俘虏不仅为公孙瓒筑了易京,还为公孙瓒屯田,提供了大量的粮食,据说有三四百万石,够吃十年。”
易京在易县,在围堑十重,引水为池。围堑之间建楼,高五六丈,有将士据守。最中心的楼高十丈,由公孙瓒本人居住,兼作粮仓。
进攻这样的阵地,对任何人来说,都是一个头疼的问题。强攻的伤亡将非常可观,围而不攻反而是最稳妥的办法。
唯一的问题是公孙瓒储存了大量的粮食。就算够吃十年有虚张声势的成份,打个对折,五年也够久的。
围城五年,想想都让人觉得头皮发麻。
看完地图,荀攸虽然心里很震惊,脸上却看不出太多的情绪。“子刚,你觉得刘和不肯与袁绍决裂,是因为报仇,还是因为其他的?”
阎柔说道:“报仇。”他顿了顿,又道:“我想不出他有什么的理由。”
荀攸无声地笑了。“那他会失望的,袁绍攻不下易京。”
“监军呢?”阎柔反问道。
“以目前的兵力而言,我也攻不下易京。”荀攸抚着凳下的短须。“但帮刘和报仇并非必须攻克易京不可。”
“不攻下易京,怎么报仇?”
“易京中的粮食再多,也不可能吃一辈子。再者,公孙瓒之所以固守易京,也是因为相信袁绍不会长久,只要能坚持到袁绍败亡,他自然可以幸免。可若是他知道就算袁绍败亡了,朝廷也不会放过他呢?”
阎柔愕然。
荀攸笑道:“在他一个人死,和族灭之间,他会选择哪一个?”
阎柔明白了荀攸的意思,却更加为难。“监军的意思是说,如果刘和向朝廷称臣,报仇只须朝廷一纸诏书?”
荀攸点点头,又劝道:“子刚,你们为故主报仇,这当然是义举。可是义举之外,却不能忘了君臣大义。刘和不从大义,朝廷又何必成全他的私义?你别忘了,于朝廷而言,公孙瓒固然有擅杀大臣之罪,却也守边有功。功过相抵,本不至于必死。若他肯悔过自新,天子给他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,也未尝不可。为了一个依附袁绍的人,诛杀有功之臣,恐怕说不过去。”
阎柔苦笑。如此一来,岂不成了死结?
荀攸拍拍阎柔的肩膀。“还有,你们除了报仇之外,也要将眼光放得长远一些,想想幽州的将来。是追随朝廷,为中兴建功,还是追随袁绍,与袁绍一起灭亡,这可不是一家一姓的小事,当三思而行。我再说一句不好听的,就算袁绍得了天下,你们就能富贵吗?”
阎柔想起了赵云的话,心中有了决断。
第四百六十三章 名与实
对幽州人来说,与袁绍结盟只是为了报刘虞被杀之仇,并不是看好袁绍本人。相反,他们对袁绍的所作所为并不认同,也不觉得袁绍得了天下就是好事。
只不过幽州实力有限,而袁绍的影响力又太强,让他们兴不起反对的心思,不得不委曲求全。
现在情况不同了,少年天子逆风翻盘,接连取得大捷,而袁绍去年南下却遭受挫败,传檄而定天下的设想成了笑话。
仅就为刘虞报仇而言,朝廷也比袁绍有把握。
既然如此,幽州人又何必和袁绍搅在一起?
阎柔去过并州、凉州,见过天子,也知道天子的边郡政策,当然清楚这才是对幽州最好的政策,有可能实现边郡的长治久安,远非袁绍的一味怀柔可比。
袁绍将宗族女嫁给了乌桓、鲜卑首领为妻,又封他们为单于,却对幽州人的利益置之不顾。将来他若得了天下,幽州将不再是幽州人的幽州,而是鲜卑人、乌桓人的幽州,说不定会落得和凉州的境地,被那些大臣们抛弃。
两相一对比,并不难做出选择。
阎柔委婉的表示,幽州人的目的是为刘虞报仇,并不想与朝廷为敌。如果刘和一意孤行,他们可以独立行事,并不一定要与刘和共进退。
荀攸表示赞赏,但这不是阎柔一个人的表态就能说明问题的,至少要等幽州人与袁绍划清界限再说。
荀攸随即又说,你是乌桓司马,与乌桓人很熟悉,有没有兴趣来帮我?鲜卑人暂时安稳了,乌桓人却还没有俯首称臣,我想请你出面,宣示朝廷的心意。如果能说服乌桓人和袁绍划清界限,避免刀兵,也是一项善举。
阎柔欣然从命。
如果能让乌桓人称臣,对他个人来说有功,对公孙瓒来说,则是加速了死亡。乌桓人对公孙瓒的仇恨极深,有他们从旁声援,公孙瓒会死得更彻底,就算朝廷想给他将功赎过的机会,也要面对更强的反对声音。
送走了阎柔,荀攸随即上书,向天子汇报幽州的新形势。
虽然他也觉得易京不易攻取,但袁绍率领主力赶来,必然会大大加强战斗的进程。在无法与公孙瓒取得联络的情况下,不能让袁绍的进攻太顺利,从其他方向予以牵制是顺理成章的选择。
如果能把握得好,或许可以成为反攻的契机,取得比去年更大的战果。
——
“当年被他俘虏的青州黄巾。”阎柔说道:“三十万人,最后剩下的不到三成。那些黄巾俘虏不仅为公孙瓒筑了易京,还为公孙瓒屯田,提供了大量的粮食,据说有三四百万石,够吃十年。”
易京在易县,在围堑十重,引水为池。围堑之间建楼,高五六丈,有将士据守。最中心的楼高十丈,由公孙瓒本人居住,兼作粮仓。
进攻这样的阵地,对任何人来说,都是一个头疼的问题。强攻的伤亡将非常可观,围而不攻反而是最稳妥的办法。
唯一的问题是公孙瓒储存了大量的粮食。就算够吃十年有虚张声势的成份,打个对折,五年也够久的。
围城五年,想想都让人觉得头皮发麻。
看完地图,荀攸虽然心里很震惊,脸上却看不出太多的情绪。“子刚,你觉得刘和不肯与袁绍决裂,是因为报仇,还是因为其他的?”
阎柔说道:“报仇。”他顿了顿,又道:“我想不出他有什么的理由。”
荀攸无声地笑了。“那他会失望的,袁绍攻不下易京。”
“监军呢?”阎柔反问道。
“以目前的兵力而言,我也攻不下易京。”荀攸抚着凳下的短须。“但帮刘和报仇并非必须攻克易京不可。”
“不攻下易京,怎么报仇?”
“易京中的粮食再多,也不可能吃一辈子。再者,公孙瓒之所以固守易京,也是因为相信袁绍不会长久,只要能坚持到袁绍败亡,他自然可以幸免。可若是他知道就算袁绍败亡了,朝廷也不会放过他呢?”
阎柔愕然。
荀攸笑道:“在他一个人死,和族灭之间,他会选择哪一个?”
阎柔明白了荀攸的意思,却更加为难。“监军的意思是说,如果刘和向朝廷称臣,报仇只须朝廷一纸诏书?”
荀攸点点头,又劝道:“子刚,你们为故主报仇,这当然是义举。可是义举之外,却不能忘了君臣大义。刘和不从大义,朝廷又何必成全他的私义?你别忘了,于朝廷而言,公孙瓒固然有擅杀大臣之罪,却也守边有功。功过相抵,本不至于必死。若他肯悔过自新,天子给他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,也未尝不可。为了一个依附袁绍的人,诛杀有功之臣,恐怕说不过去。”
阎柔苦笑。如此一来,岂不成了死结?
荀攸拍拍阎柔的肩膀。“还有,你们除了报仇之外,也要将眼光放得长远一些,想想幽州的将来。是追随朝廷,为中兴建功,还是追随袁绍,与袁绍一起灭亡,这可不是一家一姓的小事,当三思而行。我再说一句不好听的,就算袁绍得了天下,你们就能富贵吗?”
阎柔想起了赵云的话,心中有了决断。
第四百六十三章 名与实
对幽州人来说,与袁绍结盟只是为了报刘虞被杀之仇,并不是看好袁绍本人。相反,他们对袁绍的所作所为并不认同,也不觉得袁绍得了天下就是好事。
只不过幽州实力有限,而袁绍的影响力又太强,让他们兴不起反对的心思,不得不委曲求全。
现在情况不同了,少年天子逆风翻盘,接连取得大捷,而袁绍去年南下却遭受挫败,传檄而定天下的设想成了笑话。
仅就为刘虞报仇而言,朝廷也比袁绍有把握。
既然如此,幽州人又何必和袁绍搅在一起?
阎柔去过并州、凉州,见过天子,也知道天子的边郡政策,当然清楚这才是对幽州最好的政策,有可能实现边郡的长治久安,远非袁绍的一味怀柔可比。
袁绍将宗族女嫁给了乌桓、鲜卑首领为妻,又封他们为单于,却对幽州人的利益置之不顾。将来他若得了天下,幽州将不再是幽州人的幽州,而是鲜卑人、乌桓人的幽州,说不定会落得和凉州的境地,被那些大臣们抛弃。
两相一对比,并不难做出选择。
阎柔委婉的表示,幽州人的目的是为刘虞报仇,并不想与朝廷为敌。如果刘和一意孤行,他们可以独立行事,并不一定要与刘和共进退。
荀攸表示赞赏,但这不是阎柔一个人的表态就能说明问题的,至少要等幽州人与袁绍划清界限再说。
荀攸随即又说,你是乌桓司马,与乌桓人很熟悉,有没有兴趣来帮我?鲜卑人暂时安稳了,乌桓人却还没有俯首称臣,我想请你出面,宣示朝廷的心意。如果能说服乌桓人和袁绍划清界限,避免刀兵,也是一项善举。
阎柔欣然从命。
如果能让乌桓人称臣,对他个人来说有功,对公孙瓒来说,则是加速了死亡。乌桓人对公孙瓒的仇恨极深,有他们从旁声援,公孙瓒会死得更彻底,就算朝廷想给他将功赎过的机会,也要面对更强的反对声音。
送走了阎柔,荀攸随即上书,向天子汇报幽州的新形势。
虽然他也觉得易京不易攻取,但袁绍率领主力赶来,必然会大大加强战斗的进程。在无法与公孙瓒取得联络的情况下,不能让袁绍的进攻太顺利,从其他方向予以牵制是顺理成章的选择。
如果能把握得好,或许可以成为反攻的契机,取得比去年更大的战果。
—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