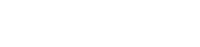头依旧疼得厉害,让谢征不自觉皱眉。
信最后到了魏祁林手中,这其中是不是还发生了什么?只是朱有常也不知道了。
他面上愈是苍白,愈显平静,已问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,便道:“魏严勾结反贼,已被李家弹劾,不日便要在金銮殿上被问责,朱将军且先好生休养,十七年前的血债,本侯会向魏狗一一讨回来的!”
-
从朱有常住处离开后,谢忠一直亦步亦趋跟着谢征,几番欲言又止。
雨势渐小,从回廊檐瓦上坠下的,只剩一片珠帘似的细小水珠子。
谢征一身褚袍,单手负于身后,静立于檐下看着院中一片浓翠青竹,俊秀的眉眼间似漫不经心,又给人以满身清贵都压不住那股沉郁煞气的心惊之感。
谢忠踌躇再三,终究还是开了口:“侯爷……”
谢征眼皮不动,只说:“不用跟着我,下去吧。”
谢忠难得逾越道:“夫人当年之举,想来也是为了保全侯爷,不得已而为之,侯爷莫要伤怀,将军和夫人泉下若知侯爷如今的本事,也会含笑的。”
谢忠眼神陡然冷戾:“下去。”
谢忠抬眸看了一眼谢征冷硬的背影,在心底轻叹一声。
他一直都知道,谢夫人的自缢,是谢征解不开的一个心结。
如今真相大白,于谢征而言,只怕会更加痛苦。
过去的十几年里,他恨谢夫人软弱,恨她狠心抛下他,任他被仇人教养长大。
可谢夫人却是在撞破魏严的阴谋后,为了保全朱有常和谢家旧部自缢的。
魏严可以关朱有常等人一辈子,却总不能关自己的亲妹妹一辈子。而只要谢夫人还活着,谢征就终有一日会知道当年的真相。
以魏严的手段,大抵只会斩草除根。
谢夫人是为了保谢征的命,才选择了自缢,她留下遗言让魏严教养谢征,也是想把谢征送到魏严眼皮子底下,让魏严彻底放心。
一年前谢征听到那些传言,开始重查锦州一案,魏严也的确设了死局,想让他死在崇州平叛之战中。
让他憎恨又想念了十几年的母亲,其实是为他而死,谢忠不知自己眼前这位从少年时期,就用单薄的肩膀扛起整个谢家荣辱的青年人内心会痛苦成什么样。
他清楚谢征的性子,有再多宽慰的话也不知从何说起,拱手朝谢征一拜后,终是退下了。
偌大的回廊空荡荡只余谢征一人,冷风又刮了起来,吹得细雨斜飞,飘进廊下,擦过他苍白的脸庞,只留一片冰凉的湿意。
谢征背靠廊柱,支起一条腿坐到了木质栏杆上,浓黑的长睫半覆下来如扇,一瞬不瞬望着远处竹叶上的雨水因汇聚了太多,承载不住从叶尖往下滴落。
他试着很努力去回想,但还是记不起那个女人的样貌了,脑海里只有个模糊的影子在很温柔地笑,似乎这世间没什么过错在她那儿是不能得到原谅的。
可她留给他最后的记忆,只剩他站在门口,从房内望去飘荡在空中的半截裙摆。
这个场景在无数个夜晚里折磨着他,让他冷汗涔涔惊厥着从噩梦中醒来。
他恨她软弱自私,她却是为了保他而去的。
额前的碎发被冷风吹到了眼睑处,谢征微扬起头,抬手覆在了眼前,维持了这个姿势很久,一动不动。
-
魏府。
这一场秋雨,仿佛要洗净天地尘垢。
魏府的高门华屋前,亮着两盏灯火,隐在夜幕里的桐杨浓阴中,好似一双猩红兽眼。
书房窗前一地野菊在冷风凄雨里挺立着花骨朵儿,瘦弱的花茎苦苦支撑着,说不清是傲骨还是执拗。
满朝皆知魏严爱菊,却又不喜那些名贵的花种,独爱漫山遍野随处可见的野菊。
整个丞相府,种得最多的,也是那一长就长一片的野菊,凭着那堪称蛮横的长势,府上的下人打理稍微怠惰了些,野菊就能逼得花圃里其他花草无处生长。
案前铺着三尺暖光,筋骨强劲的老者提笔阅卷,在秋雨未停的凉夜只着一件单衣,身形也不显单薄。
跪在下方的人浸着冷汗将白日里的事禀报:“……有两拨人前来劫狱,您多年寻常州虎符未果,是朱有常将虎符缝进了自己的断腿里。前一波人带他出狱时,被天字号的人缠住,他双腿行走不便,怕拖累那些人,捡了把匕首剜开腿肉,将虎符取与了那些人……”
“后又杀来一拨人,看武功路数,应出自谢家,他们趁天字号去追拿走了虎符的前一拨人,救走了朱有常……”
老者笔下未停,昏黄烛光映出的墨迹,方遒有力,一勾一横宛若屈铁断金。
时人崇尚行草,入仕之人则以写得一手好台阁体而备受推崇,魏严却是以一手瘦金体闻名。
字如其人,瘦筋硬骨。
没听到老者出言,跪在下方的人额前冷汗越聚越多,在未知的恐惧达到顶点时,朝着案前重重一叩首,前额抵在冰冷的地砖上,颤声道:“请丞相责罚!”
老者终于停了笔,朝下方投去淡淡一瞥:“自己去刑室领罚。”
魏府豢养的死士,进一次刑室无异于丢半条命,跪在下方的人听到老者此言,在此刻却只有捡回一条命的狂喜。
他朝着老者再次一叩首后,悄无声息退出了书房。
侍者上前帮老者洗墨笔,低声道:“相爷,当年的事……只怕瞒不住了。”
魏严起身,踱步至窗前,任冷风灌满衣袖猎猎作响,颤抖的烛火将他投下的影子拉得格外颀长,恍若山岳。
他望着满院萧瑟冷雨中的野菊道:“给宫里递信,是时候让西征大军进京受封了。”
第129章
秋意一浓,北地的天便日渐冷了下来,清晨起来,院中落光了叶子的榆杨枝头都凝着一层白霜。
樊长玉养伤的这一月里,身上的衣裳已从夏日的薄衫换成了厚实的秋衣。
她当日为了保护俞浅浅母子,撞伤了背部,短时间内不能舞刀弄枪,干躺着又无趣得紧,便又看起了晦涩难懂的四书五经。
其实她对兵书的兴趣更大些,但兵法中所提及的排兵布阵,有的还得精通星象分野和地理山水,看得樊长玉很是头疼,只能循序渐进,先啃入门级的那些书。
长宁从前跟着西席认字,尚且三天打鱼两天晒网,眼下一看樊长玉每天手不释卷,又有俞宝儿这个玩伴在,顿时又提起了读书的兴趣,跟俞宝儿比谁认的字多。
余宝儿都能背一些简单的诗文了,长宁自是比不过他,那股争强好胜的心气儿一上来,长宁直嚷着要找先生教她读书。
之前暂住崇州时给她请的西席,在她回蓟州后没一起跟过来。
眼下她们又没个稳定的落脚处,给她重新请西席的事,樊长玉才暂且搁置了。
俞宝儿倒是自告奋勇说愿意教长宁,但小孩奇怪的自尊心作祟,死活不肯,樊长玉读过的书不多,字却是被她娘逼着认全了的,便自个儿教起了长宁。
俞宝儿很好学,每天都去樊长玉房里跟着念书。
两个小孩经常比着背诗文,看谁背得更快,通常都是俞宝儿更甚一筹,长宁急得差点掉眼泪,但又要面子,不好意思哭,便晚上抱着自己的枕头偷溜去樊长玉房里,说是想跟樊长玉一起睡,其实是为了开小灶提前背诗文,弄得樊长玉哭笑不得。
靠着这法子,长宁总算是赢了俞宝儿几回,奈何俞宝儿背得很快,原本一天只学一篇诗文,后面两个小孩都会背了,俞宝儿就提出学两篇。
长宁靠着作弊才赢他几次,本来就心虚,想拒绝又给不出个理由,捏着衣角哼哼唧唧不吭声。
樊长玉是个缺根筋的,眼见长宁赶上了进度,觉着两个小孩都学得快,一天学两首诗文也没什么,便同意了。
于是背两首诗的这天,长宁没啥意外地又输了。
赵大娘做了点心给她们送来时,长宁搬了个小马扎背对着她们坐在墙角,头顶的揪揪都往下耷拉着。
赵大娘笑着问:“宁娘这是怎么了?小嘴撅得都能挂油瓶了。”
樊长玉捧着一卷书坐在躺椅上晒太阳,闻言笑答:“她跟宝儿比着背书,比输了。”
赵大娘招呼长宁过去吃点心,笑呵呵道:“过来吃大娘做的马蹄糕,宁娘可是宝儿小姑姑呢,让着宝儿是应该的。”
长宁“咦”了一声,惊讶了转过脑袋来,兴奋地盯着俞宝儿道:“我是你小姑姑!”
俞宝儿也是头一回听到小姑姑这个说法,他稚气的小眉头一皱:“宁娘比我小,不应该是长宁妹妹吗?”
赵大娘笑得合不拢嘴:“辈分可不是按年纪算的,你唤长玉一声姑姑,宁娘同长玉是姐妹,那不就是你小姑姑了吗?”
长宁人小鬼大,知道自己在辈分上占了俞宝儿便宜,立马开心了起来,笑得见牙不见眼,对俞宝儿道:“快叫小姑姑!”
樊长玉看着这对活宝,不免摇头失笑。
俞宝儿抿了抿唇,突然看向樊长玉:“那我不叫长玉姑姑了,叫长玉姐姐。”
樊长玉手中的书页刚翻了一页,听到俞宝儿的问话,一时间颇有些哭笑不得:“那可不行。”
俞宝儿一张脸没从前那般圆润了,拧起眉头时,隐约已有了几分小少年的样子,他不解地问:“为什么?”
樊长玉道:“你唤我姐姐了,那我跟你娘可不就差了一辈了?”
俞宝儿闷闷地不说话了。
只有长宁得瑟得嘴角都飞了起来。
日头升高后,屋檐和枯枝上的晨霜都化开了来,晨曦泄进屋内,长宁和俞宝儿捧着书又开始摇头晃脑地读,樊长玉莞尔看了一会儿,在躺椅上舒服地伸了个懒腰。
谢五从院外进来禀报道:“督尉,有贵客来访。”
樊长玉微微扬眉,暗道在这蓟州,还能有谁会来自己这儿?
须臾,便见一身白袍,肩头搭着银鼠皮大氅的公孙鄞从庭外信步而来,在这深秋寒月里笑得如沐春风:“自一线峡战场上一别后,当真是许久不见了,樊姑娘官至督尉,今日总算是能亲口向樊姑娘道一声恭喜。”
见来者是公孙鄞,樊长玉着实有些意外,她起身相迎:“公孙先生可是稀客。”
俞宝儿没见过公孙鄞,有些警惕地看着面生的俊美男人。
长宁却是迈着短腿跟个小炮仗似的直接朝着公孙鄞扎了过去,欢喜叫道:“公孙叔叔!”
公孙鄞揉了揉长宁头顶的揪揪,很诚恳地评价:“你这头发终于扎整齐了。”
长宁晃了晃发髻上的铃铛绒花,说:“是赵大娘扎的。”
公孙鄞道:“猜到了。”
樊长玉在一旁尴尬轻咳一声,打断一大一小的谈话道:“寒舍简陋,公孙先生随意坐。”
赵大娘看出樊长玉这是有公事要谈,哄着两个孩子随自己出去了。
谢五帮公孙鄞沏了杯茶,樊长玉问:“先生不是在康城么,怎的突然来了蓟州?”
公孙鄞浅抿一口热茶,挑眉道:“樊姑娘还没得到消息?陛下下旨,要让平叛有功的将军们都上京受封了。”
樊长玉说:“我这段时日都在养伤,没去军中当值,的确还不知这消息。”
她好奇问:“公孙先生过来同大军汇合,是要一起进京吗?”
公孙鄞手中折扇一开,高深莫测道:“公孙家不涉朝堂,我来这里,是受谢九衡之托。”
信最后到了魏祁林手中,这其中是不是还发生了什么?只是朱有常也不知道了。
他面上愈是苍白,愈显平静,已问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,便道:“魏严勾结反贼,已被李家弹劾,不日便要在金銮殿上被问责,朱将军且先好生休养,十七年前的血债,本侯会向魏狗一一讨回来的!”
-
从朱有常住处离开后,谢忠一直亦步亦趋跟着谢征,几番欲言又止。
雨势渐小,从回廊檐瓦上坠下的,只剩一片珠帘似的细小水珠子。
谢征一身褚袍,单手负于身后,静立于檐下看着院中一片浓翠青竹,俊秀的眉眼间似漫不经心,又给人以满身清贵都压不住那股沉郁煞气的心惊之感。
谢忠踌躇再三,终究还是开了口:“侯爷……”
谢征眼皮不动,只说:“不用跟着我,下去吧。”
谢忠难得逾越道:“夫人当年之举,想来也是为了保全侯爷,不得已而为之,侯爷莫要伤怀,将军和夫人泉下若知侯爷如今的本事,也会含笑的。”
谢忠眼神陡然冷戾:“下去。”
谢忠抬眸看了一眼谢征冷硬的背影,在心底轻叹一声。
他一直都知道,谢夫人的自缢,是谢征解不开的一个心结。
如今真相大白,于谢征而言,只怕会更加痛苦。
过去的十几年里,他恨谢夫人软弱,恨她狠心抛下他,任他被仇人教养长大。
可谢夫人却是在撞破魏严的阴谋后,为了保全朱有常和谢家旧部自缢的。
魏严可以关朱有常等人一辈子,却总不能关自己的亲妹妹一辈子。而只要谢夫人还活着,谢征就终有一日会知道当年的真相。
以魏严的手段,大抵只会斩草除根。
谢夫人是为了保谢征的命,才选择了自缢,她留下遗言让魏严教养谢征,也是想把谢征送到魏严眼皮子底下,让魏严彻底放心。
一年前谢征听到那些传言,开始重查锦州一案,魏严也的确设了死局,想让他死在崇州平叛之战中。
让他憎恨又想念了十几年的母亲,其实是为他而死,谢忠不知自己眼前这位从少年时期,就用单薄的肩膀扛起整个谢家荣辱的青年人内心会痛苦成什么样。
他清楚谢征的性子,有再多宽慰的话也不知从何说起,拱手朝谢征一拜后,终是退下了。
偌大的回廊空荡荡只余谢征一人,冷风又刮了起来,吹得细雨斜飞,飘进廊下,擦过他苍白的脸庞,只留一片冰凉的湿意。
谢征背靠廊柱,支起一条腿坐到了木质栏杆上,浓黑的长睫半覆下来如扇,一瞬不瞬望着远处竹叶上的雨水因汇聚了太多,承载不住从叶尖往下滴落。
他试着很努力去回想,但还是记不起那个女人的样貌了,脑海里只有个模糊的影子在很温柔地笑,似乎这世间没什么过错在她那儿是不能得到原谅的。
可她留给他最后的记忆,只剩他站在门口,从房内望去飘荡在空中的半截裙摆。
这个场景在无数个夜晚里折磨着他,让他冷汗涔涔惊厥着从噩梦中醒来。
他恨她软弱自私,她却是为了保他而去的。
额前的碎发被冷风吹到了眼睑处,谢征微扬起头,抬手覆在了眼前,维持了这个姿势很久,一动不动。
-
魏府。
这一场秋雨,仿佛要洗净天地尘垢。
魏府的高门华屋前,亮着两盏灯火,隐在夜幕里的桐杨浓阴中,好似一双猩红兽眼。
书房窗前一地野菊在冷风凄雨里挺立着花骨朵儿,瘦弱的花茎苦苦支撑着,说不清是傲骨还是执拗。
满朝皆知魏严爱菊,却又不喜那些名贵的花种,独爱漫山遍野随处可见的野菊。
整个丞相府,种得最多的,也是那一长就长一片的野菊,凭着那堪称蛮横的长势,府上的下人打理稍微怠惰了些,野菊就能逼得花圃里其他花草无处生长。
案前铺着三尺暖光,筋骨强劲的老者提笔阅卷,在秋雨未停的凉夜只着一件单衣,身形也不显单薄。
跪在下方的人浸着冷汗将白日里的事禀报:“……有两拨人前来劫狱,您多年寻常州虎符未果,是朱有常将虎符缝进了自己的断腿里。前一波人带他出狱时,被天字号的人缠住,他双腿行走不便,怕拖累那些人,捡了把匕首剜开腿肉,将虎符取与了那些人……”
“后又杀来一拨人,看武功路数,应出自谢家,他们趁天字号去追拿走了虎符的前一拨人,救走了朱有常……”
老者笔下未停,昏黄烛光映出的墨迹,方遒有力,一勾一横宛若屈铁断金。
时人崇尚行草,入仕之人则以写得一手好台阁体而备受推崇,魏严却是以一手瘦金体闻名。
字如其人,瘦筋硬骨。
没听到老者出言,跪在下方的人额前冷汗越聚越多,在未知的恐惧达到顶点时,朝着案前重重一叩首,前额抵在冰冷的地砖上,颤声道:“请丞相责罚!”
老者终于停了笔,朝下方投去淡淡一瞥:“自己去刑室领罚。”
魏府豢养的死士,进一次刑室无异于丢半条命,跪在下方的人听到老者此言,在此刻却只有捡回一条命的狂喜。
他朝着老者再次一叩首后,悄无声息退出了书房。
侍者上前帮老者洗墨笔,低声道:“相爷,当年的事……只怕瞒不住了。”
魏严起身,踱步至窗前,任冷风灌满衣袖猎猎作响,颤抖的烛火将他投下的影子拉得格外颀长,恍若山岳。
他望着满院萧瑟冷雨中的野菊道:“给宫里递信,是时候让西征大军进京受封了。”
第129章
秋意一浓,北地的天便日渐冷了下来,清晨起来,院中落光了叶子的榆杨枝头都凝着一层白霜。
樊长玉养伤的这一月里,身上的衣裳已从夏日的薄衫换成了厚实的秋衣。
她当日为了保护俞浅浅母子,撞伤了背部,短时间内不能舞刀弄枪,干躺着又无趣得紧,便又看起了晦涩难懂的四书五经。
其实她对兵书的兴趣更大些,但兵法中所提及的排兵布阵,有的还得精通星象分野和地理山水,看得樊长玉很是头疼,只能循序渐进,先啃入门级的那些书。
长宁从前跟着西席认字,尚且三天打鱼两天晒网,眼下一看樊长玉每天手不释卷,又有俞宝儿这个玩伴在,顿时又提起了读书的兴趣,跟俞宝儿比谁认的字多。
余宝儿都能背一些简单的诗文了,长宁自是比不过他,那股争强好胜的心气儿一上来,长宁直嚷着要找先生教她读书。
之前暂住崇州时给她请的西席,在她回蓟州后没一起跟过来。
眼下她们又没个稳定的落脚处,给她重新请西席的事,樊长玉才暂且搁置了。
俞宝儿倒是自告奋勇说愿意教长宁,但小孩奇怪的自尊心作祟,死活不肯,樊长玉读过的书不多,字却是被她娘逼着认全了的,便自个儿教起了长宁。
俞宝儿很好学,每天都去樊长玉房里跟着念书。
两个小孩经常比着背诗文,看谁背得更快,通常都是俞宝儿更甚一筹,长宁急得差点掉眼泪,但又要面子,不好意思哭,便晚上抱着自己的枕头偷溜去樊长玉房里,说是想跟樊长玉一起睡,其实是为了开小灶提前背诗文,弄得樊长玉哭笑不得。
靠着这法子,长宁总算是赢了俞宝儿几回,奈何俞宝儿背得很快,原本一天只学一篇诗文,后面两个小孩都会背了,俞宝儿就提出学两篇。
长宁靠着作弊才赢他几次,本来就心虚,想拒绝又给不出个理由,捏着衣角哼哼唧唧不吭声。
樊长玉是个缺根筋的,眼见长宁赶上了进度,觉着两个小孩都学得快,一天学两首诗文也没什么,便同意了。
于是背两首诗的这天,长宁没啥意外地又输了。
赵大娘做了点心给她们送来时,长宁搬了个小马扎背对着她们坐在墙角,头顶的揪揪都往下耷拉着。
赵大娘笑着问:“宁娘这是怎么了?小嘴撅得都能挂油瓶了。”
樊长玉捧着一卷书坐在躺椅上晒太阳,闻言笑答:“她跟宝儿比着背书,比输了。”
赵大娘招呼长宁过去吃点心,笑呵呵道:“过来吃大娘做的马蹄糕,宁娘可是宝儿小姑姑呢,让着宝儿是应该的。”
长宁“咦”了一声,惊讶了转过脑袋来,兴奋地盯着俞宝儿道:“我是你小姑姑!”
俞宝儿也是头一回听到小姑姑这个说法,他稚气的小眉头一皱:“宁娘比我小,不应该是长宁妹妹吗?”
赵大娘笑得合不拢嘴:“辈分可不是按年纪算的,你唤长玉一声姑姑,宁娘同长玉是姐妹,那不就是你小姑姑了吗?”
长宁人小鬼大,知道自己在辈分上占了俞宝儿便宜,立马开心了起来,笑得见牙不见眼,对俞宝儿道:“快叫小姑姑!”
樊长玉看着这对活宝,不免摇头失笑。
俞宝儿抿了抿唇,突然看向樊长玉:“那我不叫长玉姑姑了,叫长玉姐姐。”
樊长玉手中的书页刚翻了一页,听到俞宝儿的问话,一时间颇有些哭笑不得:“那可不行。”
俞宝儿一张脸没从前那般圆润了,拧起眉头时,隐约已有了几分小少年的样子,他不解地问:“为什么?”
樊长玉道:“你唤我姐姐了,那我跟你娘可不就差了一辈了?”
俞宝儿闷闷地不说话了。
只有长宁得瑟得嘴角都飞了起来。
日头升高后,屋檐和枯枝上的晨霜都化开了来,晨曦泄进屋内,长宁和俞宝儿捧着书又开始摇头晃脑地读,樊长玉莞尔看了一会儿,在躺椅上舒服地伸了个懒腰。
谢五从院外进来禀报道:“督尉,有贵客来访。”
樊长玉微微扬眉,暗道在这蓟州,还能有谁会来自己这儿?
须臾,便见一身白袍,肩头搭着银鼠皮大氅的公孙鄞从庭外信步而来,在这深秋寒月里笑得如沐春风:“自一线峡战场上一别后,当真是许久不见了,樊姑娘官至督尉,今日总算是能亲口向樊姑娘道一声恭喜。”
见来者是公孙鄞,樊长玉着实有些意外,她起身相迎:“公孙先生可是稀客。”
俞宝儿没见过公孙鄞,有些警惕地看着面生的俊美男人。
长宁却是迈着短腿跟个小炮仗似的直接朝着公孙鄞扎了过去,欢喜叫道:“公孙叔叔!”
公孙鄞揉了揉长宁头顶的揪揪,很诚恳地评价:“你这头发终于扎整齐了。”
长宁晃了晃发髻上的铃铛绒花,说:“是赵大娘扎的。”
公孙鄞道:“猜到了。”
樊长玉在一旁尴尬轻咳一声,打断一大一小的谈话道:“寒舍简陋,公孙先生随意坐。”
赵大娘看出樊长玉这是有公事要谈,哄着两个孩子随自己出去了。
谢五帮公孙鄞沏了杯茶,樊长玉问:“先生不是在康城么,怎的突然来了蓟州?”
公孙鄞浅抿一口热茶,挑眉道:“樊姑娘还没得到消息?陛下下旨,要让平叛有功的将军们都上京受封了。”
樊长玉说:“我这段时日都在养伤,没去军中当值,的确还不知这消息。”
她好奇问:“公孙先生过来同大军汇合,是要一起进京吗?”
公孙鄞手中折扇一开,高深莫测道:“公孙家不涉朝堂,我来这里,是受谢九衡之托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