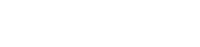很快,学子又意识到另外一件严重的事:那件御赐之物若为“祢衡”所有,祢衡的来历定然不简单。他们殴打祢衡,岂不是……
第22章狂士楚歌
哪怕学子已经隐约意识到深层次的问题,开始后悔自己过多的坦白,此刻也无济于事。
他不能收回已经说出口的话,更不可能决定他人的选择。
最终,如他所预料的那样,在得知坦白从宽,且覃绰利用他们盗窃稀有珍宝后,所有同伙者供认不讳,承认了罪行。
一部分人单纯不忿覃绰挑唆利用他们,还想让他们背锅;另一部分人则暗恨覃绰竟然独吞宝物,没有分给他们半点好处。
不管出发点是什么,出于利己本性,他们都不会搭上自己,和覃绰一起承担他们事先并不知情的“盗窃罪”。
被晾在案堂的覃绰绞尽脑汁地想办法为自己脱罪,刚想出些许头绪,就收到了同谋几人的认罪,不由傻眼。
同谋几人自以为撇清了盗窃之事,单论伤人罪最多被羁押几天,略作处罚。哪知他们写完认罪,竟被告知他们“打伤铜鞮侯,等候发落”,同样傻了眼。
不是,这铜鞮侯是哪里来的?难不成说的是祢衡?祢衡他是铜鞮侯!?
伤人者震惊无措,县尉与县令也好不到哪里去。
他们原先听“祢衡”报案——说他不但被打,还丢了御赐之物——尽管因为涉及御赐之物而不得不予以重视,但他们根本没往“祢衡”的身份上想,只以为他出自簪缨之家,祖上有人做过官,得过皇帝的赏赐,这才有一件御赐的珪瓒。
因此,县尉与县令对郑平虽然客气,但这客气只是基于祢衡本人的恶劣名声,是为了避免麻烦,不愿招惹对方的假客气,极度浮于表面。
当最后收集好犯事者的证词,县官们准备结案的时候,郑平突然取出代表铜鞮侯的金印,差点把所有县官吓得忘记呼吸。
世人常说“天下辐裂,诸侯并起”,可这时候的诸侯并非真正的“诸侯”,不过是一个戏称。真要说起来,唯有彻侯才能及得上“诸侯”二字。
秦汉爵制,彻侯为首。彻侯又分县、乡(都乡)、亭(都亭),以县为尊。
铜鞮侯正是县侯,享有封邑,甚至能以县立国,非乡侯、亭侯可比。
虽说整个大汉江山,可以拎出的县有一大堆,但是能封县侯的,若不是宗室,便是于汉朝有大功劳的功臣及功臣的后裔。
以东汉特殊的立国背景,除了个别几个权势滔天的宦官,能成为县侯的人,身家背景与世家人脉都不会简单。
因此,历任县侯都是东汉公主的最佳择偶候选,无一例外。
如今哪怕已是今非昔比,连年的战火将尊卑等级变作了一纸荒唐,即便是天子也横遭侮辱,沦为董卓等手中的傀儡。然而东汉未亡,仍为正统,士人们仍敬奉天子,遵循汉之教化。
不管众人心中是如何作想,至少表面上皆遵从原有的阶级与礼教,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。
而有曹操率先带头,重拾天子之尊,虽不知他这份心意能坚持多久,就目前而言,没人敢在许都对皇家权威不敬。
县衙的几个县官不过是食俸百石的小官,有的还不足百石,哪里经得住县侯的阵仗,再看郑平的时候,简直连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。
唯有与县尉一同从隔壁房间出来的荀彧神色自若,一如原先的那般:不因为祢衡恶名昭彰而退避三舍,心生偏见;也不因为他的身份骤然逆转,成为食禄万户的侯爵而多一分看重。
他只态度平常地与郑平见了一个士礼,温厚坦荡。
郑平以士礼回之,在与他错身而过之前,淡淡地道了一句:“多谢。”
一分惊讶之色自那双潭水般清透的眼中划过,荀彧抬头而视,只看到郑平快步离去的背影。
他忽然知道了郑平在谢什么。
“他如何而知?”
郑平因为那罐伤药特地又谢了荀彧一次。不止口头上的言谢,他也将这份好意记在心中。
汉律繁冗,打伤平民和打伤彻侯当然不会是同一个处罚。当年的董卓再嚣张,也没敢殴打皇帝,就连汉少帝刘辩也是他悄悄毒死的。后来事泄乃是情不得已,若当时能够追究,董卓早死了一万次。
何况此案还牵扯了御赐之物的盗窃案,主犯覃绰势必会得到严惩,从犯的几人也讨不到好。
纵然死罪可免,也得接受髡首剃发之刑,送去建造部门“劳改”。
且不说覃绰等人在知道真相后是怎样的一副心情,当远在司空府的曹操收到县衙亲信传来的情报,亦是吃惊不小。
他虽然早就通过孔融对祢衡的态度察觉到祢衡身份的不简单,但他也只把祢衡当成孔融这样的名流之后,没想到他还袭了侯爵之位。
第22章狂士楚歌
哪怕学子已经隐约意识到深层次的问题,开始后悔自己过多的坦白,此刻也无济于事。
他不能收回已经说出口的话,更不可能决定他人的选择。
最终,如他所预料的那样,在得知坦白从宽,且覃绰利用他们盗窃稀有珍宝后,所有同伙者供认不讳,承认了罪行。
一部分人单纯不忿覃绰挑唆利用他们,还想让他们背锅;另一部分人则暗恨覃绰竟然独吞宝物,没有分给他们半点好处。
不管出发点是什么,出于利己本性,他们都不会搭上自己,和覃绰一起承担他们事先并不知情的“盗窃罪”。
被晾在案堂的覃绰绞尽脑汁地想办法为自己脱罪,刚想出些许头绪,就收到了同谋几人的认罪,不由傻眼。
同谋几人自以为撇清了盗窃之事,单论伤人罪最多被羁押几天,略作处罚。哪知他们写完认罪,竟被告知他们“打伤铜鞮侯,等候发落”,同样傻了眼。
不是,这铜鞮侯是哪里来的?难不成说的是祢衡?祢衡他是铜鞮侯!?
伤人者震惊无措,县尉与县令也好不到哪里去。
他们原先听“祢衡”报案——说他不但被打,还丢了御赐之物——尽管因为涉及御赐之物而不得不予以重视,但他们根本没往“祢衡”的身份上想,只以为他出自簪缨之家,祖上有人做过官,得过皇帝的赏赐,这才有一件御赐的珪瓒。
因此,县尉与县令对郑平虽然客气,但这客气只是基于祢衡本人的恶劣名声,是为了避免麻烦,不愿招惹对方的假客气,极度浮于表面。
当最后收集好犯事者的证词,县官们准备结案的时候,郑平突然取出代表铜鞮侯的金印,差点把所有县官吓得忘记呼吸。
世人常说“天下辐裂,诸侯并起”,可这时候的诸侯并非真正的“诸侯”,不过是一个戏称。真要说起来,唯有彻侯才能及得上“诸侯”二字。
秦汉爵制,彻侯为首。彻侯又分县、乡(都乡)、亭(都亭),以县为尊。
铜鞮侯正是县侯,享有封邑,甚至能以县立国,非乡侯、亭侯可比。
虽说整个大汉江山,可以拎出的县有一大堆,但是能封县侯的,若不是宗室,便是于汉朝有大功劳的功臣及功臣的后裔。
以东汉特殊的立国背景,除了个别几个权势滔天的宦官,能成为县侯的人,身家背景与世家人脉都不会简单。
因此,历任县侯都是东汉公主的最佳择偶候选,无一例外。
如今哪怕已是今非昔比,连年的战火将尊卑等级变作了一纸荒唐,即便是天子也横遭侮辱,沦为董卓等手中的傀儡。然而东汉未亡,仍为正统,士人们仍敬奉天子,遵循汉之教化。
不管众人心中是如何作想,至少表面上皆遵从原有的阶级与礼教,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。
而有曹操率先带头,重拾天子之尊,虽不知他这份心意能坚持多久,就目前而言,没人敢在许都对皇家权威不敬。
县衙的几个县官不过是食俸百石的小官,有的还不足百石,哪里经得住县侯的阵仗,再看郑平的时候,简直连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。
唯有与县尉一同从隔壁房间出来的荀彧神色自若,一如原先的那般:不因为祢衡恶名昭彰而退避三舍,心生偏见;也不因为他的身份骤然逆转,成为食禄万户的侯爵而多一分看重。
他只态度平常地与郑平见了一个士礼,温厚坦荡。
郑平以士礼回之,在与他错身而过之前,淡淡地道了一句:“多谢。”
一分惊讶之色自那双潭水般清透的眼中划过,荀彧抬头而视,只看到郑平快步离去的背影。
他忽然知道了郑平在谢什么。
“他如何而知?”
郑平因为那罐伤药特地又谢了荀彧一次。不止口头上的言谢,他也将这份好意记在心中。
汉律繁冗,打伤平民和打伤彻侯当然不会是同一个处罚。当年的董卓再嚣张,也没敢殴打皇帝,就连汉少帝刘辩也是他悄悄毒死的。后来事泄乃是情不得已,若当时能够追究,董卓早死了一万次。
何况此案还牵扯了御赐之物的盗窃案,主犯覃绰势必会得到严惩,从犯的几人也讨不到好。
纵然死罪可免,也得接受髡首剃发之刑,送去建造部门“劳改”。
且不说覃绰等人在知道真相后是怎样的一副心情,当远在司空府的曹操收到县衙亲信传来的情报,亦是吃惊不小。
他虽然早就通过孔融对祢衡的态度察觉到祢衡身份的不简单,但他也只把祢衡当成孔融这样的名流之后,没想到他还袭了侯爵之位。